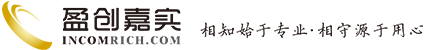
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,居民财富不断增加,越来越多人投入投资理财的世界,并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收获更多财富。今天,我们就跟着经济学动态发布的《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中期报告》来探讨下高增长、高积累过程中国民财富的规模扩张与结构变化。

01
居民财富的积累
自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居民财富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开始积累,并在10余年来持续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。
在新千年伊始,中国居民财富同GDP之比不足3倍,明显低于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。其间,虽然受到2008年危机的短暂冲击,但得益于高储蓄、高增长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,中国这一比率大体上保持了持续上升的态势,至2016年已经达到4.3倍,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。
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,财富的快速积累使居民成为国民财富的最大持有部门,这也符合许多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。然而,由于经济体制特点等因素——如不能取得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完整所有权、公有制经济占有主导地位等,中国居民财富占国家总体财富的比重仍相对较低,至2016年仅约为73%,而主要发达国家同类指标达到近90%。相应地,中国广义公共部门的财富相对规模较大,达到近27%。
尽管不能简单地据此判断孰优孰劣,但这一差异对于理解中国居民经济行为特点、宏观收入分配、税负以及金融风险分布及其应对等关键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正是由于这一“不平衡”的差距,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倾向可以得到部分解释。由于财富存量较少,中国居民通过储蓄进行财富积累(如购买住房资产)、抑或预防不时之需的动机(即预防性储蓄)较强烈。
02
居民财富规模扩张与结构变化
在规模扩张的同时,中国居民财富呈现出若干重要的结构特征。
例如,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启的住房市场化改革、快速城市化等推动下,住房构成了中国居民总资产的最大单项——在金融危机前占比超过一半,明显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。
尽管在金融深化和房地产调控的过程中,这一占比在10余年间有所下降,但自2014年起,在城市土地供应趋紧、城市化继续推进等因素的作用下,住房资产相对规模又开始缓慢回升。在此需要强调的是,对住房资产的较高依赖,会使居民储蓄及负债行为同房价和相关调控政策等高度关联,极不利于风险-收益的分散化管理,从而制约财富长期、稳定的增长。
当然,居民对住房资产的“热衷”,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体制特点及金融发展程度使然:即在长期的高增长过程中,居民部门持续积累财富,但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其积累途径较为有限,尤其是难以通过土地、矿藏等自然资产以及海外资产的形式实现。

换言之,优质、安全资产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居民对持有住房偏好不减的主因之一。这部分地解释了历次旨在“控房价”的政策措施成效不彰。从全国整体看,经过10余年的调控,城市(特别是重点城市)住房资产仍旧是最主要的私人财富附着物或价值储藏载体。只要这一基本性质没有根本上的改变,住房的“金融属性”也难以削弱。
鉴于此,为实现2018年7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”这一要求,应注重“疏”“堵”结合:简单地“限购”“限售”“限贷”很难取得明显成效,甚至还可能强化升值预期。从长远计,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发展资本市场、支持实体经济等举措,形成财富积累的新渠道、新载体。
随着金融业的发展、深化,中国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构成也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。
2004-2016年,居民持有的现金、存款(含公积金存款)、债券等金融资产项目占比持续下降:其中,现金由7%降至3%、存款由51%降至36%、债券由5%降至2%。相应地,居民“理财”几乎从无到有,至2016年已占金融资产的13%。证券投资基金也从1%骤升至8%、保险准备金占比从3%升至5%、股票及股权等维持在20%左右。
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构成同美国迥异,后者现金、存款、债券三项合计仅约为20%,其他大部分项目为“股权投资”和“保险及养老金等”,占比分别约为50%和30%。如此的结构变化与差异,随着中国金融深化与创新的持续进行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可以通过持有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,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并进行相应的流动性与风险管控。
当然,在逐渐替换现金、存款、债券等较为“传统”的价值储藏、投资增值途径的过程中,居民金融资产的流动性、风险水平及其传导机制等都会发生相应改变,享有的金融服务更为繁复、迂回,相应的信息成本、管理成本、道德风险等都在提高。
需要指出的是,同样为发达国家,日本、德国的现金、存款、债券等项目在居民金融资产中仍占有很大比重(分别约占55%和40%),且近年无明显方向性变化。而这两国一般被认为是实体经济高度发达、金融系统较为稳健的经济体。所以,尽管金融资产结构可作为评判金融发展水平、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等的分析视角,但必须辩证对待——特别是要在风险-收益之间进行权衡,不存在单一、静止的优劣评价标准。